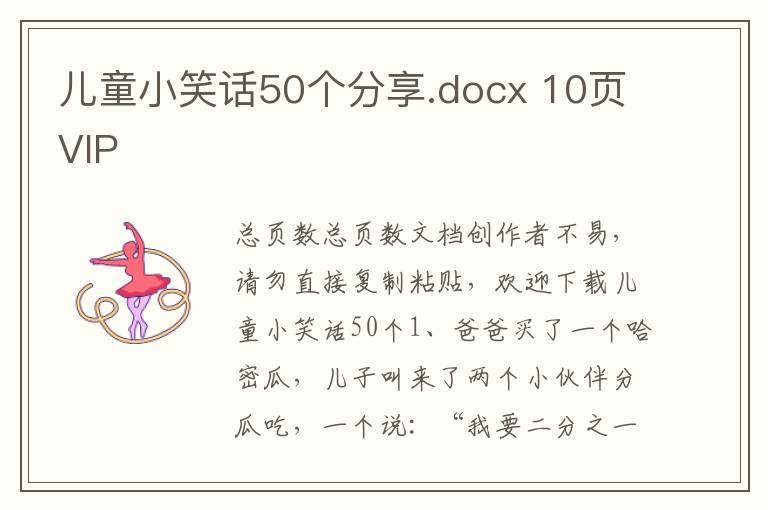抗战相声,老舍原来还是个段子手

抗战陪都重庆有一个抗战曲艺潮,其中的“抗战相声”堪称重庆特产,像毛肚火锅一样诞生于重庆,还有老舍这样的大名家亲自上阵支持,还产生了欧少久、董长禄(小地梨)师徒这样的抗战相声名家,今天我们说说当时老舍在重庆说相声和写相声的故事。
票友
据《老舍年谱》所载史料,1938年8月老舍先生从沦陷的武汉撤退到重庆,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,1946年2月底赴美讲学,抗战时期老舍在重庆呆了近8年。
老舍在重庆先后住在大梁子青年会、白象街88号《新蜀报》和南泉,1943年最后搬到北碚蔡锷路24号(现天生新村63号附16号)小楼。
老舍北碚旧居
这里原是林语堂买的房子,他到美国去了,就送给老舍住。老舍在此住得最久,写了一代名著《四世同堂》前两部《惶惑》和《偷生》,还写了一箩筐话剧、散文、杂文、曲艺、诗词,相声虽然不是最多,但却最有年代感。
1945年,老舍摄于重庆北碚寓所外。
我在北平有一位朋友,是个票友。此人这京戏呀,迷得厉害,一心想“下海”,成名角儿。可他是个左嗓子,唱得太差,谁听了谁捂耳朵。没办法,只好自个儿找个清静的地界儿——跑到西山去唱。上了装,提把青龙偃月刀,连做带打,唱关云长《单刀赴会》。正唱着,打山上下来一个老头儿,打柴的樵夫。一看这位,吓蒙了:不知是关老爷显圣,还是土匪劫道,赶忙跪下磕头:“好汉爷饶命!好汉爷饶命!”票友一看,心中暗喜,大喝一声:“老头儿休怕!饶尔等性命不难,只须——听我一段西皮倒板——便可免你不死”。随即便又野唱起来。但唱着唱着,樵夫“扑通”一声又跪下了:“好汉爷,你甭唱了,还是杀、杀了我吧!”票友惊问:“为何?”老头哭道:“我觉得,还是杀了我更好受”。老舍是一个老资格的相声票友了。1924年去伦敦讲学,也把相声带去,和中国同学演过传统段子《大保镖》、《黄鹤楼》,可能是相声在英国最初的表演记录。1930年他回国先后在齐鲁大学、山东大学任教。据《齐鲁晚报》2015年01月29日李耀曦《老舍在齐鲁大学说相声》一文回忆:齐大国文系1933级学生张昆河先生亲口讲述,老舍在一次师生联欢会上打了一趟很接地气的山东查拳后,就登台开说单口相声《票友》,笑翻全场——
2006年央视春晚侯耀华和郭达演的一个小品《戏迷》,构思和“包袱”,都跟老舍当年说的《票友》撞上了,可能他们都“偷”的是同一个相声老段子。
敲头
梁实秋先生《忆老舍》一文就写了他和老舍在北碚说相声的故事。
抗战后,梁实秋差不多和老舍同时到重庆,主持《中央日报·平明副刊》,在国立编译馆上班。他对老舍的语言很赞:“只觉得他以纯粹的北平土语写小说颇为别致。北平土语,像其他主要地区的土语一样,内容很丰富,有的是俏皮话、歇后语,精到出色的明喻暗譬,还有许多有声无字的词字。”
他还白描了老舍的战时形像:“他又黑又瘦,甚为憔悴,他身体不大好,患胃下垂,平常总是佝偻着腰,迈着四方步,说话的声音低沉,徐缓,但是有风趣……生活当然是很清苦的……老舍对谁都是一样的和蔼亲切,存心厚道,所以他的人缘好,但是内心却很孤独。”“他离开北碚不久有一封信给我,附近作律诗六首,诗写得不错,可以从而窥见他的心情,他自叹中年喜静,无钱买酒,半老无官,文章为命,一派江湖流浪人的写照。”
老舍和梁先生在北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作说相声时,是快乐的,也是惊险的。那是北碚一个募款劳军晚会,梁先生出面邀请清同治年间著名昆曲正旦钱金福的弟子姜作栋,和沈从文的小姨妹、礼乐馆多才多艺的张充和,合演昆曲《铁冠图》的一个折子戏《刺虎》,“在这一出戏之前,要垫一段对口相声。这是老舍自告奋勇的。蒙他选中了我做搭档,头一晚他 逗哏 我 捧哏 ,第二晚我 逗哏 他 捧哏 。事实上,挂头牌的应该是他。他对相声特别有研究。在北平长大的,谁没有听过焦德海、草上飞?但是能把相声全本大套的背诵下来,则并非易事。”
老舍给他面授了说相声的诀窍,还顺手把两个段子写出来,一段是《新洪羊洞》,一段是《一家六口》,都是老相声。“相声里面的粗俗玩笑,例如 爸爸 二字刚一出口,对方就得赶快顺口答腔地说声 啊 ,似乎太无聊,但是老舍坚持不能删免,据他看,相声已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,不可稍有损益。”
但有一点老舍还是让了步:里面有一个规定动作,逗哏老舍要用折扇敲打捧哏梁的头一下。“是我坚决要求,他才同意在用折扇敲头的时候只要略为比划而无需真打。
到了上演那一天,我们走到台的前边,泥塑木雕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,观众已经笑不可抑。”
但到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,梁先生发现老舍“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,还是有意违反诺言”,抡起大折扇狠狠地向自己打来,显然是老舍为了相声艺术,决定牺牲梁实秋:“我看来势不善,向后一闪,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镜,说时迟,那时快,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,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,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,喝彩声历久不绝,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,还高呼: 再来一回! ”
月饼
据曾与侯宝林合著《曲艺概论》的相声理论家汪景寿先生《老舍和相声的缘分》一文考证:1938年8月老舍一到重庆,就举办了两期通俗文艺讲座,先后创作了《卢沟桥战役》、《台儿庄大捷》、《维生素》、《新对联》、《欧战风云》、《骂汪精卫》等相声段子,和流亡到重庆的北方相声演员欧少久、董长禄(小地梨)师徒在书场里表演,很受欢迎。
1939年春天,在重庆电影制片厂联欢晚会上,老舍亲自登台与欧少久表演相声《中秋月饼》,又加演一段老舍编写的相声《绕口令》,效果爆棚,引起《大公报》的关注,称这些节目为“抗战相声”。
《绕口令》今已失传,相声《中秋月饼》后来由欧少久口述、殷文硕记录整理,编入了《老舍文集》第13卷,并注:相声《中秋月饼》是老舍于1938年在重庆编写的。
《中秋月饼》定场诗引用一首民间小调:“月儿弯弯照九州,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几家高楼饮美酒,几家流落在街头?”然后利用月饼的传统馅料味型比如五仁、豆沙、枣泥、叉烧、火腿、洗沙来抖包袱,把时政主旋律和传统相声的谐音手法巧妙结合,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——
乙:您把月饼馅子,又比喻什么呢?
甲:我略举几种,比如:“五仁”——就是说日寇侵华罪行,惨无人(五仁)道……
日寇的三光政策:杀光、烧光、抢光,从月饼馅子里,都能看出来……“豆沙”——见人“都杀”;“洗沙”(洗杀)——洗劫一空,再来杀害;“枣泥”,就是把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,糟(枣)蹋得和泥(泥)土一样……
乙:太可恨了……
欧少久、董长禄(小地梨)师徒,带着这段把美食和战争一锅烩的相声,在成渝等地巡演,到处爆棚,曾遭有关当局禁演。
精心遴选,每日推送,欢迎打开微信,搜索公众号“长城曲艺网”,更多精彩,不见不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