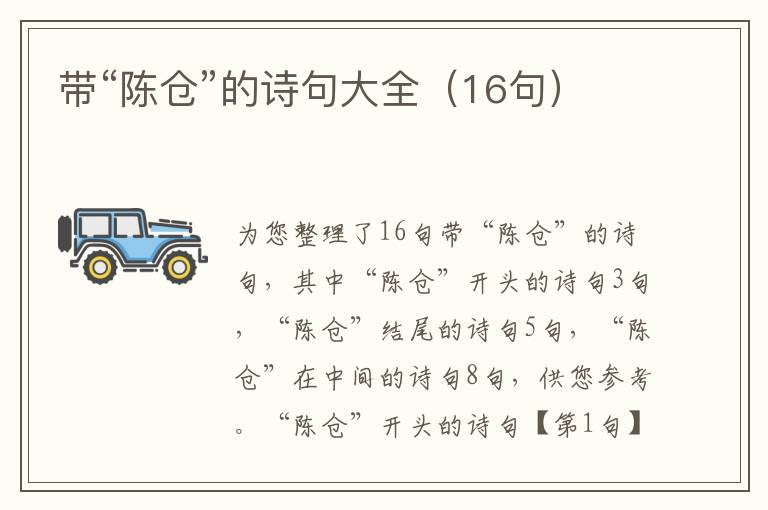腊月二十九洗澡说说精选80条

过年洗澡的抒情散文
旧时,人们无论有钱无钱,过年时总要理个发,洗个澡的。即便到了今天,年前的洗澡,大约也是必要的程序。通过洗澡,人们可以干净整洁地去辞旧迎新,以一种愉快的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,而年一过,新的生活,新的征程又要开启了。
今年二月八日,当我从省城风尘仆仆地赶回二百多里外的家时,正是农历腊月二十八的时候,仅隔一天就过年了。当我到家时,妻早已准备好换洗的衣服及毛巾洗涤用品了。我匆匆忙忙地喝了点茶,吃点东西,就去了离家不远的一处公共洗澡堂洗澡——其实,在家里也可以洗澡,因为家里早已安装了燃气淋浴,但我总觉得到公共澡堂洗澡能洒得开,更主要的还是,过年时在公共澡堂里的洗澡,人虽多,但大家在忙碌中仍透着安详与从容,内心都充溢着喜悦的.心情,有一种过年洗澡时的那种特有的氛围。
是的,过年洗澡,不似平常那么急急忙忙的了,人虽众多但心情都很安详,节奏大多也是很舒缓的。澡堂里,有四十多岁的男人带着七八十岁的老人,也有年青一点的父亲,带着小不点儿的儿子,也有象我一样的,独自一人,大家彼此虽不相识,但只要目光相接,皆柔和祥瑞,因为这是年前的最后一次洗澡了,洗完澡就快快乐乐地过年了。老人们很安静地,或泡在澡堂的大水池时,或站在淋浴喷头下,一切皆听从带着他们的男人的安排与吩咐,象一个听话的小孩儿。当然,那男人也很细心地给老人搓着背、洗着身子,洗好后,给老人穿衣。人或许老了,腿脚胳膊不灵是自然的,所以穿衣时是一件较困难与麻烦的事,然而,那些男人们却极有耐心地打理着,不似平时那么心急火燎的,这大约也与过年洗澡时的心情有关吧。小孩们则不同了,他们或大呼小叫地从一头跑到另一头,或哭喊着要从大水池里挣扎着出来,总之不那么安静了,但孩子们的嘻闹或哭喊,却也增加了过年前的那种忙碌氛围,平添了一种喜庆的色彩,因为孩子们急着洗完澡,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放礼花鞭炮了。记得我小的时候,也在这样一个年关的时候,因家里根本没有淋浴器之类的东西,村子里也没有公共大澡堂,但故乡的人们过年总还是要洗澡的,怎么办呢?故乡的人们很聪明,他们早就打好了一个大木桶,长约两米多,宽约一米五左右,呈椭圆形,内置连接在一起的四方木凳,可坐三四人。到了腊月二十八九的时候,母亲总是烧好了两大桶热水,有时在热水里还放入一定的香喷喷的艾蒿叶,由父亲挑着来到放在村里集体屋里的大木桶前。父亲先把大木桶清洗一下,塞好塞子,然后就把两桶热水倒入大木桶中,最后我们便一个个地进入,通常由父亲把我们抱入里面的,盖上大盖子,就算是过年洗澡了。由于木桶是基本上封闭的,人在里面任由热气薰蒸,不一会儿就感到浑身燥热,再过一会儿,用毛巾在浑身上下擦洗一下,所有的垢渍全部洗去,根本不用打肥皂或沐浴剂之类的,身上一下子仿佛轻了许多,等出了大木桶后,身上还冒着缕缕地热气,脸色红彤彤的,真是舒服极了。时正夕阳西下,通红的余辉照在脸上,相互辉映,走在弥漫着极浓郁年味的村子里,人生好象达到极乐的境界。洗完澡,就过年了,我们得到一些五毛或一元的压岁钱,接着便与其它小伙伴们在村里随意放着五颜六色的鞭炮,一个个快乐得象小天使一般。
如今,故乡过年洗澡用的大木桶是否还存在着,我不得而知了,但儿时过年洗澡的情景仿佛如昨,印象极其深刻。自然,离开故乡后,每年过年时还是要洗澡的,只是形式上的,或象征性的意义更多了点了,每次过年洗澡,总感到那不是在洗澡,而是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,通过洗澡,把一年来所有的不快与晦气连同那身上的污垢,一起擦去,擦出一个新的心情,擦出一个新的盼头,涤出一个全新的面貌,一个全新的身子。
有时我想,倘我们的心灵也象过年洗澡那样,定期地去洗一洗,那将是心灵世界中的一个多么快乐地升华过程,那将是洗出一个多么干净美丽心灵的过程!而干净的心灵,又将给世界带来多么美好的希望!而这个美丽的希望,不正是人间处处企盼着的温馨之爱么?
过年幸福的抒情散文
幸福不是得到了多少,而是谁把你的心弦拨动,感动了多少。
初三那天,小妹夫打电话说已经出发,先到弟弟处,次日能来。我便早早准备起来。晚上弟弟微信:明天中午能够到达。我列出了迎接他们午餐的菜谱。我合计,大妹二妹家各来一位,弟弟全家,加小妹一家,八九个人吧。吃的没问题。住也没问题,找单位招待所。还有进出场区的通行,该找找小张了,她爱人是警卫营的教导员。
一早就紧张地准备进来。菜是现成的,过节前做了充分准备,加之之前弟弟妹妹处带来的牛羊猪肉,丰盛得不能再丰盛了。考虑到现在大家吃的油厚肉多,特别地多弄了些开胃素菜。这只能用我的感受代替别人的感受。打电话找小张,把车号要过来发过去;再电话问招待所所长有没有住的地方,预定了两到三间房子。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一切准备工作做好,心里就踏实下来。虽然弟弟打电话说差不多1点才能到达,但那一早的时间过得尤其快。几乎还没顾得上歇一下,他们通过检查站的电话已经打来了。
他们一路平安,一路顺利。听到他们摁响门铃的声音,迎着他们络绎不绝进门的.身影,我的心被拨动着,感动着。
弟弟和他高大的儿子,小妹全家和驾车的小杨师傅,二妹和她的小儿子,大妹的小女儿和大女婿。他们集合着队伍来看望我,给我拜年,怎么能不让我感动?!
很紧凑地吃饭、喝酒。饭后联系他们去参观载人航天发射场。抓紧准备晚饭,听妹妹妹夫跟在一群孩子后边喊着好冷回家来,坐在一起看电视玩手机吃干果水果吵吵嚷嚷,就回到曾经过年的氛围里。
这多像是父母还在时候,我们都团聚在家里的景象!我和弟弟围着父亲玩牌,孩子们你呼我嚷地打闹,妹妹们跟母亲弄了这个吃的弄那个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跟我到小城之后的第一个春节,妹妹和弟弟就来了,就这样团聚过。母亲逝世后,这样的大团聚,是五年来的第一次,我怎么能不非常高兴呢?
快吃晚饭了,弟弟要返回,带走了侄儿还有大妹的女儿女婿,说到大妹处再吃晚饭,就告别他们。晚饭后一起玩会儿扑克牌,听外甥和儿子在一起说学习工作恋爱的事情。次日早餐后他们到弱水河边看冰,快十一点回来一起包了饺子。巧的是,破五不少人讲究的正是饺子。午饭后他们辞别,我给妹妹弟弟们带了我自己加工的食品,眼看着他们绝尘而去。
我觉得这个年过得尤其幸福,这个幸福是由妹妹弟弟们一起来团聚中得来的,是我精心为他们做的每一顿饭里得来的。看着他们把菜吃得干干净净,我尤其高兴。我想,过去,父母也是这样看我们回家吃东西,返回时再拿着各种吃食走的吧。
我高兴没到饭馆去。开始爱人说,是不是到饭馆定一桌,显得正式一些。我说不用了,啥东西都有,自己做的又安全放心,何必要去破费?再说,过年讲究在家,自己做饭就显出家的味道来。做的好孬都不重要,重要的这是我的心意,让他们能感觉到家的味道。
假若跑饭馆里吃一顿,吃完了浸入到寒风里走回家来,刚刚升腾的热情便会全部冷却。轻松是轻松了,省事是省事了,但过年团聚的氛围将大不一样。现在感觉,在家里把冰柜里的食物腾空一些,把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奉献出来给他们吃了,特别地快乐幸福。这是在饭馆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感受,也是完全无法让弟妹们找到家的意思的。
这个年获得的幸福当然不止于此,还有儿子给我们带来的冲锋衣,我们让儿子穿的羊毛衫;以及儿子坦然地讲他的工作、找朋友的各种情况。儿子显然长大了些,能够开诚布公而不是缄默不语,有自己的想法标准而不是人云亦云。孩子一年有一年的进步,这是做父母最值得高兴的事情,是大年收到的最好礼物。
还有一家人的健康平安。无论我们工作生活里有多少曲折复杂,过年能得来团圆健康平安和睦,就是最值得庆幸、值得珍重的。哪怕我们的日子极其平淡,工作平凡收入不高,但我们有健康,知足长乐,懂得感恩,就能感觉出前所未有的幸福来。现在,无论我的小家庭还是我们兄弟姊妹亲戚朋友中,虽然没有大富大贵,但家家和睦,人人健康,个个平安,难道不是最幸福的么!
还有得到的一些特别祝福。那些文友们、那些圈友们的真诚祝福祝愿,都成为这个春节感人至深的幸福时刻。一句话的事情,绝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,这是人与人最近的距离,这是人与人间最无私的赠予,怎么能不令人感动不已!
过年的幸福,标志着生命中付出与获得的价值。感受幸福越多,说明获得越多,曾经付出也多。今天,我越来越相信,付出是多么美好,获得是多么幸福。
生活中的随意汇聚,就变成了我在这个春节期间的莫大幸福。
过年的抒情散文
该过年了,父亲的电话也多了起来。母亲年轻时劳苦忙碌,累下了一身的病痛。春节的准备工作大半落在了父亲身上。弟弟、弟媳也都带着孩子回来了,买东西跑腿的事倒还可以,关键是生食变成熟食就是个问题了。好在今年我放假早,正好去给父母帮帮忙。
这几年在外打工,每年忙得不知所以,一直要到年三十,才开始包饺子过年。今年可好,父母搬来县城居住,二十三,母亲烙好了发面馍,早早地就给我送了过来。自打结婚以来,和父母相隔两地,多年没吃上母亲烙的馍了。想起小时候,一进入腊月二十三,学校放了假,我和弟弟就巴望着过年,一天天地数着日子:二十三,发面火烧夹糖官儿;二十四,扫房子……,一直到初一,早早地不用母亲叫,就急着起床穿新衣,然后等着爷爷奶奶发压岁钱,然后就和小伙伴们开心地出去疯玩狂闹。
“下午过来跟我搁锅吧”。父亲打来了电话。搁锅是我们这里的方言,也就是支个油锅,然后炸些发面丸子、细粉鱼之类的。说着容易,做起来特费功夫。母亲哪能闲的住,只是她腰酸腿疼的,做一会儿就顶不住了。我和父亲边做边说笑,想起了小时候过年的情景……
小时候母亲做生意,一直要忙到腊月二十五。剩下几天,时间安排的可紧了。先得打扫房子,那时的瓦房,特别是灶房,烟熏火燎的,脏得很。这个任务多半是父亲和弟弟的,一天下来,灰头土脸的,像个老灶爷似的。然后是洗衣服,那时没有洗衣机。天可真冷,有时还下雪。下雪也得洗,不然一大堆脏衣服堆在家里咋过年呢?有一年,我手冻的老厚,圆圆的像个面包一样
下来就是蒸馍了,得蒸够半月左右的'馍吃。天冷面不开,母亲着急啊,各种办法,各种烦。紧接着就是搁锅,一个个小丸子、小松鱼,累个半死。到了年三十,才慌着剁肉、剁菜包饺子。我家人多,爷爷奶奶,我姊弟四个加上父母。往往是忙到黑咕隆咚的,才端上饺子。而那时,五爷爷家早已吃过饺子,悠闲地到处逛了。逛到我家,照例一句:“还没吃呢?”
那时候忙,可心里快活的很。为的是干完这些活,就可以过年穿新衣,吃好吃的了,特别重要的是:还有压岁钱呢!我们小孩子也是不得闲的,过年一道独特的待客菜是要我们小孩子帮忙的。
买来一堆芥菜,去皮是件很令人头疼的事。今年照例是二弟的活,只是绝对没小时候那么难办了。那时的天真冷啊,热水也少。再就是一个煤火,大人忙着蒸馍搁锅,也烧不成热水。好不容易洗净了,拿个破碗碴子,坐在那儿刮皮。冰疙瘩一样比拳头还大的芥菜疙瘩啊,吃起来窜的两眼流泪,做起来可真难啊!
今年看着二弟毫不费力的就完成了,实在是不可思议。我说小时候咋就那么傻,没有削皮刀,就不会用切菜刀吗?拿个破碗碴子一个刮半天,手都冻掉了。二弟笑了:“咋不会,大哥用切菜刀,妈不让。太浪费了,削去那么厚的皮。”得,原来是这个原因,可怜我小时候的弟弟的手啊!接下来还得用木匠做活用的刨子刨成片。一天下来,可想而知这是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啊!
小时候,我是不用搁锅蒸馍的。一来大人怕做不好,过年不吉利。二来油锅也不安全。但我也有一大堆事要做。过年了,一人一条新裤子得缝裤边,还有衣服扣子得缝牢,这个任务非我莫属。很感谢那时候干的这个活,使我以后的生活中得益多多。老公孩子的衣服扣子掉了,裤子缝儿断线了,我可以不必拿去裁缝店。甚至哪件衣服有不合适的地方,我还可以动手改造一番。
尤其令我怀念的,是那时候一大家子人过年的氛围,或者说是人文习俗。小时候爷爷奶奶没和我们住一块儿,可那时候母亲再忙,逢年过节没让爷爷奶奶做过饭。不管是端午节还是中秋节等等,经常是母亲包好饺子,第一排子,先给爷爷奶奶送去。平时两三天蒸一次馍,热气腾腾的先给爷爷奶奶送几个。儿时的我和弟弟,时不时地端着饺子,拿着馍走在路上的情景,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。想起来可算是小镇上曾经靓丽的一道风景线。
如今再看我们这一代:弟媳回来是啥活都不让干的,除了带孩子。刷个碗也是偶尔为之,更别说过年做的那些吃的了。都是母亲做好了给一大家子吃。由此倍感母亲的艰辛,也特别敬佩母亲的伟大:年轻时给老人做,给孩子做,到老了依然给孩子做,还有媳妇,孙子、孙女等。
过年了,常回家看看。带上媳妇,领着孩子,回家住住。父母既喜且忧。喜的是一大家子团团圆圆,儿子媳妇,孙子孙女,天伦之乐啊!愁的是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睡,都得父母操心。特别是初一以后的几天串亲戚,母亲往往是早上一桌,吃吃刷刷半天,中午又是一桌。大家都吃好喝好了,杯盘狼藉,垃圾遍地。一天到晚,累的够呛。真恨自己不是儿子,不能和父母住在一起。可话说回来,真的作为儿子,只怕也是如弟弟一般,娶妻生子都要父母照顾了。
小时候盼过年,如今是怕过年。看着孩子一天天的巴望着过年,犹如少时的自己;而自己过年前后的心慌,必定一如当年的父母。不管是盼也好,怕也好,年,一如既往的,如期而至。而过年的一代又一代人,也一如既往的迎接年的到来。
过年感觉的抒情散文
电话铃响的时候,我刚将自己的身子扔进沙发里,举眼望着窗外那堵矮墙上藤蔓的叶子在冷风中摇曳,然后想着一个叫羚子的人,那个站立在江南烟雨里的女子,她是我最好的朋友,也是亲人,我们有一个夜晚的对话,叙述着对彼此的想念,我们不想未来,未来是一个看不见的遥远地方,我们只凭着一种惯性穿越如烟的往事,在宁静中等待,至于在等待些什么我们也不清楚。
东东正斜靠在墙角边上翻看那本现代妇科医院的免费杂志,封面是穿皮短裙,露出半边臀部年轻女护士的火辣艳照,那是前些天,我正趴在向阳街广告牌上,百无聊赖地看着人来人往的时候,一位19岁左右的女孩子硬把它塞进我怀里,当我抬起头想看清女孩的脸时,冒似清纯的少女只给我留下一个背影,不看也罢,反正现在的女孩子大都是朦胧间是清水,努力去看,化脓似的。东东对着那本杂志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,一边笑还一边骂。电话是半年没露面的阿毛打来的,电话里说春节太郁闷了,想找人出去喝酒,半天过去硬是找不着一个人,最后就试着往我这打了,阿毛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跟我说话,正好我也闲极无聊,放下电话就扯上东东,抬屁股就出去了。
阿毛家住在城东,换了两次公共汽车才到他家所在的小区,我模糊地记得还要穿过眼前这条窄巷才到他的家,我差不多有3年没有上过阿毛的家了,原因很简单,一是离我住的`地方较远,二是他有个脾气暴躁,而且有点武术功底的老婆。他老婆家在离城不远的乡下,每年过年前她都要回老家帮忙杀猪,据阿毛说他们家杀猪从来不用刀,他老婆把拳头一握,然后冷眼瞄下猪脑袋,一声嚎叫拳头像闪电般朝猪脑袋直落下去,猪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去见它祖爷爷去了。今年他老婆还有公休没休完,杀完猪就顺便在老家呆到元宵,而阿毛就自己留在城里过年了。
我已记不得具体的门牌号,我和东东在巷子里几经打听才找到他住的那栋楼,这楼原是对面电机厂的宿舍,年久失修,剥落的水泥墙已经长满了青苔。阿毛家在三楼,我们摸着爬上潮湿的楼梯,走过阴暗的过道时,东东差点迎面撞上堆在过道旁的蜂窝煤。敲了半天,才听见里面有拖鞋的声音,东东下意识跳到我的身后,阿毛披着块厚毛毯打开了房门,看见我和东东,他咧着大嘴乐了,一上来就搂着我们把我们大肆吹捧一番,把我的脸夸得热一阵冷一阵,只能以皮笑肉不笑响应,他让我们先在屋里等一下,自己到楼下的小铺去买包“红河88”,东东挨着我背后,吃力的抬起脖子,从门口往屋里四处张望,待确认什么后才贴着我的后脚跟进屋,他大概对3年前阿毛老婆赏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还记忆犹新。
我们三人坐在屋子里相对无言地抽着烟卷,见面前的那种喜悦早已荡然无存,大家似乎有很多话要说,但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或从何说起,现实的生活早就让我们的心情都变成一片黑暗。阿毛恶狠狠猛吸两口烟,浓烈的烟味呛得他剧烈的咳嗽起来,气管一阵痉挛,声音非常恐怖,我随手递过桌上一杯不知放了几天的混浊液体给他,阿毛极不耐烦地扬扬手:走走,边喝边聊。走出巷子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居然对这条巷子还是那么熟悉,学生时代我在巷子里有过一次美好但不堪回首的恋爱。
小巷拐角有一个只能放下三四张桌子的小饭铺,它周围的几间平房都开始扒了,一帮民工在换便道上的方砖。我走进铺子的时候看见门口旁边的墙砖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“3月1日前自拆”——城管大队宣。经营小饭铺的是一个60多岁的秃顶男人和他如花似玉的女儿。阿毛说这小铺本来也要拆的,只因为城管大队的队长喜欢上身上还带有点野性的女儿,后来得到满足后才应许小铺存活几天。
现在还是春节,铺里没有客人,老男人神色疲倦瘫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不停地咳嗽,女儿站在他身后轻轻揉着父亲的肩膀,看见我们进去,女孩脸上立刻扬起灿烂的笑容。
我们在一张靠窗口的桌子坐了下来,要了8两水饺,一碟炒肉片,一碟花生米,一人两瓶二锅头,边喝边聊,这时我才知道阿毛去年去了海南,本来想去干一番事业的,等到了那边就忘了自己来海南的目的了,到现在一直没想清楚自己为什么当初到了海南。差不多半年时间他都闲赋在海南一个昏暗的私人旅馆里,颓废一段时间后又从海南回到了百色,回来之后龟缩在家,心情一片灰暗。
因为大家都无事可做,我们从中午一直喝到了傍晚,吃完了饭,酒也喝足了,阿毛用纸巾一抹宽而厚的大嘴,眼皮不抬地说买单,女孩捧着账单在我们三人脸上寻摸时,大家都是目光游移不定,生怕和她的视线遭遇,直至听到东东接单,才如释重负。
那一天我们三人都喝高了,最后索性坐在马路边倾述衷肠,说到委屈处还抱头痛哭,哀叹命运不公,今天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都聊了些什么。酒精开始在胃里燃烧,我看见一张长满皱纹的脸在我面前晃。
那是我童年时老保姆的脸,她用她的手臂把我拥进怀里,我看见了摇篮,听见老保姆熟悉的心跳和夜晚迷乱的灯火,摇篮里有个幼小,活泼的生命,他在满心欢喜,我想这一定是小时候的我吧。
很晚了,该回家了,我想,可我真正的家又在哪里,脚下的路向更深沉地黑暗中延伸,望着没有尽头的黑暗,自己对自己说:春节快乐……